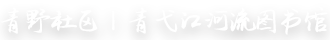“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
竹子,自古以来就在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皖南山区,竹子作为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早年间,要想把这些竹子从大山深处运出来,更多的是靠水路,也就是青弋江。
竹子能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主要和它衍生出来的一些竹制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吃喝住行,几乎都能看到竹子的身影。这就催生了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篾匠,我们称之为“竹上匠”。
青弋江水运的发达和竹林的繁茂,使得篾匠在青弋江流域蓬勃发展。青弋行者们一路走访发现,很多村落、古镇当年的篾匠活非常发达,但现在遗留下来的篾匠却寥寥无几,所见到的多是当地仅有坚守的老篾匠。他们大都沉默寡言,伏在地上,佝偻着身子,用沟壑纵横的双手麻利地编织着。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篾匠早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词。
篾匠手艺是一门细致活,要经过多年磨练才能达到精熟的程度。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劈篾,把一根完整的竹子弄成各种各样的篾,首先要把竹子劈开,再把它不同的部位做成各种不同的篾。剖出来的篾片,要粗细均匀,青白分明;编的筛子,要精巧漂亮,方圆周正;织的凉席,要光滑细腻,凉爽舒坦。
在老篾匠家中,青弋行者们看到许多种竹子。经过了解才知道,不同的编织物需要不同的竹子。而针对竹子的质量,也有所取舍。春竹不如冬竹,春竹嫩,易蛀,冬竹又要选小年的冬竹,有韧劲;不管春竹冬竹,必须要鲜竹,才能编篓打簟。刚编好的竹器还不能马上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竹子劈成较细的篾后,最外面的一层带着竹子的表皮,行话叫“青篾”,这层篾最结实,不带表皮的篾,就叫“黄篾”,黄篾比青篾的结实度相差较远,但它也有用途,像箩筐、晒箕的主要部位,由于需要量大,一般用黄篾,而竹器的受力部位,就要用青篾来做。像经常跟水接触的用具,如篮子、筲箕之类,就不能用黄篾,但它们大多取材于本地的小竹子,坚牢度不够,一般用上一年左右,就要换新。
篾匠活的精细,全在手上。一根偌长的竹子,在几声“噼啪噼啪”的响声中很快裂开了好几节,篾匠师傅破竹,像布店里撕布,潇洒利索。一双饱经沧桑的手,一来一往中,把竹丝横纵交织编成硕大的竹垫、编成圆圆的竹筛、编成尖尖的斗笠、编成鼓鼓的箩筐……
篾匠活大多是在膝盖上完成的,围裙是必不可少。老篾匠身边有一个竹篮,里面环置一竹圈,插着各式篾刀,底下是竹尺、凿子、钻子,上面有竹编的盖子。其中一件特殊的工具就是“度篾齿”,这玩意儿不大,却有些特别,铁打成像小刀一样,安上一个木柄,有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它的独特作用是插在一个地方,却能把柔软结实的篾从小槽中穿过去。
过去在农村,每家每户隔一两年就要请篾匠师傅到自己家来做活,按天数付工钱。篾匠这个营生不轻松,太苦,但是他们往往风光地上门,踏实地做事,体面地拿钱。他们的双手,粗糙似树皮,十根指头,好像十支虬盘的树根。粗糙龟裂的手,贴了五六条虎皮膏药。由于成天伏在地上编竹席,弯腰、曲背,十个篾匠九个驼,他们走起路来,佝偻着背、慢慢悠悠。
而今,这样精妙绝伦的篾匠手艺开始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就青弋江流域而言,大多数村落和古镇所见篾匠已为数不多。
常人言,农民的汗水落入土里,而篾匠的汗水却是熬尽在丝丝缕缕交织的竹蔑中。这其中,有多少苦,恐怕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一生几乎都在艰辛编织中耗去青春的篾匠,或许深深体味其中的况味,至纯朴实的他们选择用缄默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坚韧、默默无闻,如竹,代表了他们身上的品质。
调研人员:杨庆雯 倪璐瑶 李洋 杨梦凡
文字编辑:倪璐瑶 程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