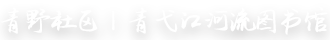安谧宁静的西河古镇六百年来静静地矗立在青弋江畔,它因水而生,因水而繁荣,却也因水而落寞。鳞次栉比的老屋早已被风雨腐蚀褪下了明丽的色彩,曾经繁荣的商铺也不见了踪影,空留下种类繁多的招牌还能看出曾经的繁华。
行者们走在那因时间冲刷而斑驳破碎的石板路上,一间用泥砖做的老房子映入眼帘,在屋子里昏黄的灯光下,一位老人端坐在桌前,干瘦却无比稳健的双手,一手拿着原料,一手握刻刀细心的雕琢着什么。被他专注的神情所吸引,我们不自觉地走上前去,才发觉是在雕刻印章。
刻章的老人姓赵,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高中刚毕业就遭遇文化大革命,不得已开始了工作。但就是在文革期间他学会了许多手艺,像雕刻、摄影、修钟表,文革结束后,赵爷爷并没有继续他的学业,在西河开一家服装店兼修表、刻章,他把这些爱好变成了工作,直到现在。几十年的风雨洗礼,让这间老店的每一处都印上了岁月的斑驳。老人桌子的左边是一个两层玻璃展柜,里面摆放着几十枚不同材质的的印章。展柜旁边摆满了各色杂物:用旧的刻刀、几盒新旧不一的印泥、一盒打磨钥匙的工具、用坏的笔、盖着印章的旧报纸。
赵爷爷回忆,刻章生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吃香,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备有私章,大家用私章代替签名领粮票、油票、布票等,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人用章,来刻章的就更少了。
刻章是一门手艺活,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刻好一枚印章,并不容易,虽然刻章的字体多用“小篆”、“隶书”和“楷体”,但是其他字体也要了解,才能满足顾客需要。赵爷爷说,刻章时需要好几把刻刀来进行雕刻,还需要练就一种执刀的方法,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人的执刀方式都不一样,需要自己去琢磨适合自己的方式。一枚印章虽然只有寥寥的几个字,但每次都要全心投入、精心雕琢。他告诉我们,其中每一笔每一划的疏密深浅、字的空间排列都非常重要,出现一点点的差错,一枚印章就毁了。赵爷爷说,这么多年,他坚持刻章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只是因为喜欢,因为这门手艺伴随他几十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早已融入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赵爷爷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如今的西河早已没有多少真正的手艺人,更没几个人还守着那传统的手艺过活了。要么退休了,要么改行了,仅剩的坚持着继续开店也是和赵爷爷年纪相仿的老人。
几十年的岁月变迁,青弋江水利交通已经不再那么便利,西河也由过去的繁华逐渐走向了衰落。过去人来人往、喧闹嘈杂的街道,如今留下的只是岁月逝去后的静谧。在赵爷爷的描述中,十几年前的西河还是挺热闹的,但是现在一年不如一年,大多数人都已经搬到旁边的镇上去了,现在整条街都已经没有多少人,大部分是老爷子老太太。这家老店的生意也早已不行,衣服鲜有人问津,机械表也仅是老一辈人的回忆,更不谈修理了。只有刻章,一个月还有四五十个,可是将来就难说了。
但老人依旧守着自家的店,守着这一片生活了六代人的土地。如今的赵爷爷已经71岁,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他的这门手艺却无人继承,两个儿子都选择外出工作,但是老人依然坚守着这一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六点多就会到店中,在那昏黄的灯光下用心雕琢着一枚枚印章。
走在西河古镇街道,总能看到一位老爷爷在那昏黄的灯光下,一直坚守在西河老街刻章,一张斑驳的桌子、几盒章具、一套刻刀,一刀一划刻了40多个春秋,这是老爷爷对刻章艺术的坚持,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坚守。
调研人员:黄胜坤 易思思 方亚玲
文字编辑:黄胜坤 叶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