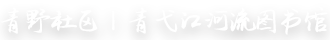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经
文化一词出自易经,而说到皖南的文化,绝对离不开泾县和太平。
泾县自古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邦”、“山川清淑,秀甲江南”之誉,地处皖南山区北部,境内山多地少。黄山余脉绵亘县境东南,九华山支脉逶迤西北,青弋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县境。这里是光荣的革命老区,皖南事变的发生地,是宣笔、宣纸的源产地。简单八个字“枕徽襟池,缘江带河”,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太平湖有着“安徽省境内唯一完整的中央直属水库”,“安徽省最大的人工湖”两个响当当的头衔。曾于湖畔发现距今7500万年的白恶纪恐龙蛋化石和新石器时代的众家山遗址,还有湖底沉睡着千年古城——广阳城、“三里秦淮”——龙门街等一大批文物古迹。“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南宋理学家朱熹题辞石刻“秀荫”至今还依旧静卧在湖畔。
提到泾、太文明,就不得不提一个人——戴新彪老师,他不光出生在皖南,而且工作在皖南,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泾、太文明的研究者。很幸运我们这次有机会拜访戴老师,一位慈祥、博学、平易近人的老者。
在和戴老师的交流中,我们收获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和青弋江相关的文化故事,甚至是推翻以前的一些认知。比如我们以为屈原是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然而真相却是他被人抓住,用麻袋绑着,扔进江中而死。如元代青花瓷的发源地竟然是在太平湖。又如《赠汪伦》诗的由来,“李白曾三游泾县,第二次路经桃花潭去往泾县,到桃花潭是应泾县县令汪伦之邀。在信中,汪伦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与汪伦一见如故。可是汪伦却诓了李白,‘桃花者,谭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乃店主人姓万也’,李白丝毫不见怪,二人饮酒赋诗,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公元前293年,我国最早的诗人屈原第二次流放就来到陵阳和现在的太平湖一带,这也是当年李白曾经想去陵阳寻仙访道的地方。
在古代,陵阳包括现在的太平湖广阳地区,历史上的龙门古镇(现在的黄山区龙门乡)与陵阳接壤。屈原很可能到过龙门地区,可惜没有留下相关诗句。屈原后来又怎么到长沙附近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呢?
据考证,屈原是遭顷襄王派人全国通缉,一人离陵阳奔赴长沙途中,不料被刺客发现,追至汨罗江上,他所乘的小舟在前,杀手在后穷追不舍。最后屈原还是被杀手抓住,装进麻袋,扔进江中。这一发现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国。
现在端午节的龙舟习俗正是再现了屈原被追杀时的激烈场面,而包粽子则是重演了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催的一幕。”
上面两段便是节选自戴老师出版的《解读泾•太之谜》一书,这本书囊括了戴新彪老师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还有汪伦的籍贯问题、太平湖(陈村水库)的建成、元代青花瓷发源地在太平湖等等有意思的发现。也许有人就会觉得文化研究很简单,翻翻资料,喝喝茶,写写文章。上文写到的似乎很有趣,可戴老师的工作却是十分枯燥。需要考经据典,经常夜不能寐,辗转多个地方,翻阅图书馆资料,查找县志,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理解、推敲,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晚上。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最终结论还可能被推翻。
当我们问到戴老师为什么对泾、太文明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戴老师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意气风发,恰好接触到几个留学生很向往中国的古诗词,他们迷恋中国文化的态度刺激了本来就酷爱文学的戴老师。在他看来,外国人尚且如此,那么身为中国人的自己,又怎能落于人后,应该更加深刻地去挖掘和全力地保护本土文化。于是,戴新彪老师投身于文化研究领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文学谜题上寻踪问迹,至今仍不忘初衷。
戴老师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即将七旬的他,学会了使用微信,时不时会发一些自己的动态,还有文化研究的新发现。同时为了更加方便地开展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推广,还学会了使用计算机。冷硬的键盘、屏幕、鼠标无疑是另一个新世界,可是戴老师做到了。也正是这份毅力,这股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念头不可阻挠,所以戴新彪老师才会在领域中硕果累累,一次次引起“轰动”。
聊天中戴老师讲了他很多关于旅游发展的观点,更让我们对眼前的这位老人心生敬意。如今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林立而起,当地政府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在发展旅游方面,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文化保护。戴老师和我们强调说:“明明皖南有这么多文化资源可以用来吸引游客,同时保护古镇文化,发展经济,一举多得,为何视而不见,甚至背道而驰呢?”
一个民族最大的资源是文化,最能打动人心的也是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最耀眼、最光亮的一定是文化,在当下时代潮流发展中能够掀起波澜的也还是文化。
而文化旅游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赏玩,也不是需要一个人对所游览的事物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它的意义所在是可以让游人能够在旅游中获得一种对生活的共鸣和感动;能够在某些瞬间和历史对话;能够不忘中国的文化底蕴;能够骨子里流动文化的血液。
戴老师为了皖南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光大贡献良多,如今我们为了保护青弋江而在夏日奔走,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有人说文化是一种信仰,对于河边长大的孩子来说,孕育文化的河流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脚步因为河流驻足,漫走在文化的光影里,不停地更新记忆,于是找到真正的自己。
调研人员:杨庆雯 程静 方亚玲
文字编辑:杨庆雯 程俊杰